

很多人认为《冰鉴》是曾国藩所写,理由来自南怀瑾的说法。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写道:“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他的没有了,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南怀瑾说的对不对呢?非常可惜,他说的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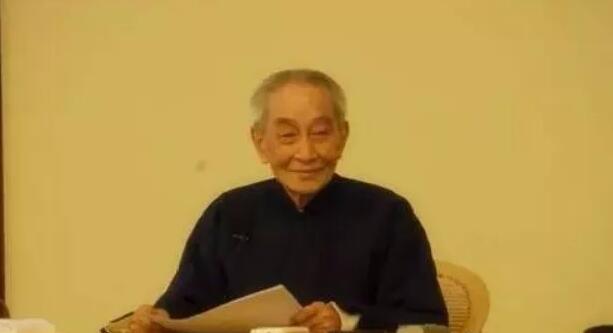
《花随人圣庵摭忆》出版于民国时期,作者黄濬。最初连载于《中央时事周报》,后来刊于《学海》,从1934年开始至1937年8月结束。此书中提到:“近人乃有以古相术《冰鉴》,傅以文正名,号为遗著,不知此书道光间吴荷屋已为锓版,叔章盖尝藏之。”意思是,《冰鉴》这本书道光年间由一个叫“吴荷屋”的人所写,假托曾国藩的名而已。所以说,民国时期就有学者指出,《冰鉴》并非曾国藩所写。为什么南怀瑾不知道呢?不为什么,只因为南怀瑾在这个问题上不严谨,以讹传讹罢了。他读了那么多国学方面的书,对曾国藩又缺乏专业的研究,出一次错也很正常。
以常理推测,如果《冰鉴》是曾国藩所写,那么必然会在曾国藩家书、日记或者其他同僚、学生等人的文字中提及。比如《挺经》,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所著《水窗春呓》就曾经说过曾国藩想写《挺经》。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所著《庚子西狩丛谈》中也曾谈及。《冰鉴》却从来没有被曾国藩自己和接近他的人谈及。再从《冰鉴》的行文风格上来看,在《冰鉴》中常见连续的四字短句,而曾国藩的家书、日记和《挺经》中很少有这样的语句。比如《冰鉴》中有“二者全无,前程莫问。”这种类似地摊看相人的常用话,难以相信出自曾国藩之口。我曾经购得光明日报出版社的《曾国藩全集》,《冰鉴》是被收藏进去的。但是,这种行文风格上的差异,引发了我的怀疑。
如果再仔细看《冰鉴》的内容,就会进一步确认这种怀疑的正确性。比如《冰鉴》说:“不千里封侯,亦十年拜相。”这种话怎么可能是曾国藩所说呢?作为一个非常低调的人,时刻担心功高震主的人,“封侯拜相”这种词汇他是很少用的。再比如“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不甚关情,亦为堕泪,妇人之仁,不足与谈心。”曾国藩是一个儒缓的人,碰到事情回复得慢一点很正常,他怎么可能批评这种态度,并且认为这种性格的人不可交呢?跟自己不太相关,但是多少有点相关,同情他人的悲剧,怎么就是妇人之仁呢?就算是妇人之仁,曾国藩也绝对不会公开说这样的人不足与谈心。如果这样说,不是显得自己很绝情么?要知道,曾国藩信奉的是老庄之道,怎么可能在自己所著的书中表现得如此绝情?再比如,《冰鉴》说:“容贵‘整’,‘整’非整齐之谓。”这就更是大大的离谱!曾国藩在日记、家书和《挺经》中多次讲到要外表整齐。比如《挺经》中开篇就提倡“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
所以说,多方证据显示《冰鉴》绝非曾国藩所写,而是他人托了曾国藩的名义写的。可惜的是,南怀瑾作为一个国学大师,在这个问题上也以讹传讹,误导了不少人。不过他读书的时候,互联网用得少,也只能从书店里买书,如果正好买到一本错误的书,一时半会也难以发现错误,于是就当真了。如果我没有事先读曾国藩的家书、日记,没有发现《冰鉴》的行文风格和内容矛盾,也不会去互联网上搜索其他人的看法。如果我只是普遍地喜欢历史,而不是特别喜欢曾国藩,可能也不会去深究,过几天我可能就在某个场合说“曾国藩的《冰鉴》中提到了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所以说,做学问一定要严谨。就像挖井一样,宁可挖深一口井,也不要处处挖几下而不深入。这个比方也是来自曾国藩家书:“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