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点评:出自《论语·述而》。孔子说,有种人什么都不知道却作假,我不是这样的。多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学习;多看,把看见的都记住。这是次一级的“知”了。
王阳明在给朋友顾璘的信中也提到了孔子这句话,但王阳明要强调的是后半句,多闻多见是“知之次”。王阳明诱导式地问,既然向外在的见闻去获取知识是知之次,那么“知之上”是什么呢?如果能够知道知之上指的是什么,就可以知道圣人做学问的用力之处了。王老师没有马上给出答案,他又引用了孔子对子贡说的话。“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意思是,子贡啊,你以为我是多学习然后能牢牢记住的人吗?不是的,我只是用一个基本道理把知识贯穿起来。此时,王阳明以反问的方式给出了答案,“一以贯之”不是致良知又是什么呢?“非致其良知而何?”为进一步加强说服力,他又引用《易经》一句话:“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思是君子通过学习过往的言行,来存养德行。在王阳明看来,畜其德就是致良知。多记住过去的言行,是致良知的具体行动。
绕了一个大圈,王阳明就是想说,向外在的见闻去求知,并不是最高级的知,最高级的“知之上”是致良知。

其实,此处王阳明曲解了孔子的意思。首先,王阳明试图将“知之上”引申为致良知,然而孔子所说的“上”指的是生而知之。孔子在劝人学习时,对学习的人的层次进行了排序。“知之上”的人,是天生就知道的圣人;其次,是学习后知道的人;再次之,是遇到困难去学习的人;而遇到困难都不去学习是下等的愚民。“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从语境来分析,孔子在说“知之次”时,附近还有一句话:“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意思是,本来没有却装作有,本来空虚却装作充实,本来贫穷却装作奢侈,这样的人是很难保持操守的。从语境来看,孔子在这里主要是批评那些不学无术、不懂装懂的人,而并非贬低向外在见闻求知的行为,也不是要为引出“知之上”而作铺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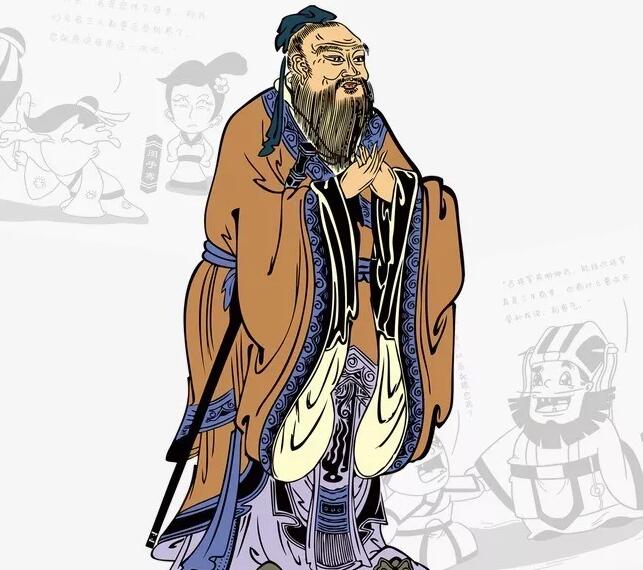
另外,孔子所谓“一以贯之”并非王阳明认为的致良知,那是什么呢?孔子在另外一个场合也提到了一以贯之。有一天,孔子对学生曾参说,我的道一以贯之。说完便出去了。其他人又问曾参,老大啥意思啊?曾子说,孔老师的学问,以“忠恕”两字贯穿始终。忠恕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有一定相似性,但不是一回事。
总之,孔子的这些话不能拿来佐证王阳明的观点。而王阳明引用了孔子的零碎语句,有移花接木的嫌疑。在《传习录》的其他地方,还能找出不少强词夺理的特征。但我们不必过于咬文嚼字,王阳明的“致良知”理论将孟子的“不动心”理论阐述得十分完善,同时进行了升华,对我们修身养性有很好的实际价值。王阳明论证其观点的过程,用现在严格逻辑来看存在很多漏洞,但是其观点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读者在阅读《传习录》的时候,没有必要去纠结每个字、每个词的意思,而是要去读懂其精神本质。王阳明心学的精神本质就是教人存养一颗纯粹的、善良的、符合天理的心,并且通过像擦拭镜子般的省察活动和实践活动来强化,追求一种不偏不倚的、不慌不乱的、不喜不悲的中庸境界,并以行动改造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