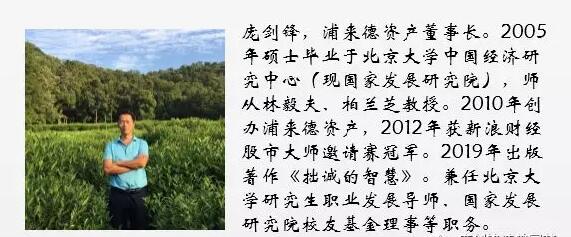有一种热心人似乎天生擅长撮合别人,不是撮合别人的婚姻,就是撮合别人的饭局,或者撮合某种业务。他就像各种社会关系的圆心,有什么事情找他,总能获得有效反馈。认识他,就相当于认识了一大群人,还不收中介费。与这样的大撮合家做朋友,真是一件幸事。在曾国藩的朋友圈中,郭嵩焘就是一个大撮合家。
(一)大撮合家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清史稿》记载,郭嵩焘字筠仙。中国近现代史专家闵杰的《晚清七百名人图鉴》与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记载,筠仙是号,伯琛才是字。到底哪个是字或者号,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

郭嵩焘和曾国藩的见面,也是被中介人刘蓉撮合的。大约在道光十六年,十八岁的郭嵩焘在岳麓书院认识了刘蓉,正好曾国藩经过长沙,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好友。“游岳麓书院,识刘蓉,而曾国藩自京师归,道长沙,与蓉旧好也,介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问学相切劘。”有空去名牌大学逛逛,多认识些优秀的朋友,还是有好处的。
郭嵩焘给曾国藩介绍的最重要的朋友,恐怕就是湘军元老江忠源了。《曾国藩年谱》记载,道光二十四年江忠源进京,通过郭嵩焘的引荐才见到了曾国藩。“八月,新宁江公忠源以公车留京师,因郭公嵩焘求见公。”这只是一笔最重要的,其他不重要的撮合案例就更多了,比如帮人做媒也很常见。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的好朋友陈岱云就请郭嵩焘做媒,想和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曾国藩写给父母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前陈岱云托郭筠仙说媒,欲男以二女儿配伊次子。”
太平军起义之后,清廷命令曾国藩去办团练,曾国藩一开始不愿意去,也是郭嵩焘出面撮合的。咸丰二年,据《清史稿》记载,当时太平军打到长沙,清廷想让曾国藩去办团练。刚开始,曾国藩一直推辞,不想去,郭嵩焘好说歹说才让他同意办团练的。“会粤寇犯长沙,曾国籓奉诏治军,嵩焘力赞之出。”怎么曾国藩别的朋友没来劝呢?可能这撮合行为是性格使然。
大概郭嵩焘善于撮合的能力在朋友圈中出了名,曾国藩竟然交给他湘军创办初期最难办的一件事——募捐,在那些有钱有官瘾的乡绅与曾国藩之间牵线搭桥。曾国藩初办湘军的时候,清廷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资金来源不是财政拨款,而是乡绅募捐。在当今太平盛世,对无财政拨款的公益机构来说,募集资金永远是重点工作之一,更何况在乱世。比如曾国藩向陶桄募款,就碰了钉子。陶桄是已经去世的两江总督陶澍的儿子,是个官后代,还是左宗棠的女婿,家底还是有些的,但是不愿意出钱。曾国藩非常生气,就写信给郭嵩焘说,想当初道光十五年我在北京,听说陶澍给京城的官员送“别敬”多达五万两银子。家里那么有钱,竟然“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曾国藩接着说,如果陶家不出三万两,我就启奏皇帝,北京还是有几个人能主持公平的,不会让你郭老弟因我而受委屈的,“无使足下为我受冤也”。大概郭嵩焘这次又充当了向陶家劝捐的中介人,所以陶家对郭嵩焘有怨气。曾国藩多年以后回忆,自己大概就是向陶家募款这件事得罪了左宗棠。
那么为什么向淘桄募款这么难呢?因为人家地位显赫,没有这个需要。真正有捐款动力的是那些没有政治地位的乡绅,弄个官的品级,充充门面嘛。曾国藩手中的资源就是“部照”,即朝廷六部发的代表品级的凭证,一种政治待遇,如果一定要类比当代,那有点类似现在的政协。能成为政协代表是一种荣誉,但没有实际的官职。有些乡绅可能不知道各种品级部照的行情,有些乡绅知道了想以同样的价格买更高的品级,有些乡绅则希望摆摆谱等着官方主动来找自己。曾国藩为了筹钱,还可以根据各种乡绅的具体诉求量身订做。于是,这种募资活动,就需要一个才思敏捷的中介来撮合。曾国藩写信对郭嵩焘说,老弟啊,你赶紧来湘潭吧,专门办理这件事,老哥我也算是用你的特长,不会让你远征去危险的地方的。“务望即日命驾前来湘潭,赶办劝捐事件。”为了加强语气,曾国藩还说,刘蓉已经跟我约好在湘潭等我,我今天也直说了,以后我不会用书信来强迫你的,“痛切直陈,此后更不以书相强矣”。
郭嵩焘还算够朋友,从咸丰四年到咸丰七年,帮助曾国藩筹集资金以及其他一些些事情。但是撮合型人才不会一直呆在某个地方,总是要经常走走才能尽兴,所以偶尔也出几趟远门,比如其间就去了一趟上海,参观了外国人所办的图书馆和轮船,可能还喝了点红酒,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感触。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回家守孝了,没有了曾大哥的军营,也没人讨论学术问题了,生活是空虚和煎熬的,郭嵩焘也回老家了。咸丰七年年底,郭嵩焘回北京了。为什么说“回”?本来他就是翰林院的编修,毕竟北京翰林院才是正式工作,和曾大哥一起打仗是兼职。咸丰八年正月初十,曾国藩给郭嵩焘的弟弟郭昆焘写的一封信,可以证明郭嵩焘去北京的时间应该是咸丰七年年底。“筠仙令兄至周家口后,有信回家否?沿途想尚平安。”
到了北京之后,可能因为有一些军事经验,郭嵩焘非常受高层重视,被选入南书房,即皇帝读书的地方。《清史稿》却讲“上书房”,即皇子读书的地方。面对与其他史料的矛盾,我个人估计,南书房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一个有军功的大臣过来陪小孩子读书有点可惜了,毕竟战争才是当时朝廷的头等大事。
在南书房,郭嵩焘还撮合了一件大事,即救了左宗棠的命。根据《清史稿》显示,左宗棠被官文弹劾,幸亏有郭嵩焘在其中周旋,找了潘祖荫,再找了肃顺帮忙,左宗棠才保住了小命。“宗棠先厄於官文,罪不测,嵩焘为求解肃顺,并言於同列潘祖荫,白无他,始获免,至是宗棠竟不为疏辨。”薛福成的《庸庵笔记》也提供更加详细的细节:郭嵩焘挺佩服左宗棠这个老乡,听到左宗棠出事赶紧去找军机大臣肃顺帮忙,但是肃顺说要有别人先上疏皇帝,自己才能开口,郭嵩焘又急忙跑去找他在南书房的同事潘祖荫。
“郭公固与左公同县,又素佩其经济,倾倒备至,闻之大惊,遣闽运往求救于肃顺。肃顺曰:‘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公方与京卿潘公祖荫同值南书房,乃挽潘公疏荐文襄。”
然后潘祖荫就向皇帝上疏,说了一句非常夸张的话:“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所以说,左宗棠的造化,离不开郭嵩焘的斡旋撮合。郭嵩焘如此地热心,不禁让后世读者怀疑他是不是收了人家的中介费。
郭嵩焘在撮合人家的时候,特别卖力。《清稗类钞》提到了郭嵩焘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推荐熊天保,“郭嵩焘字筠仙,有致江督刘文诚公坤一书,保荐熊天保。”在信德结尾,还特别强调,“因以一书代其恳求。”
近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进入同文馆做教师,也是郭嵩焘撮合的结果。《清史稿》记载,“同治七年,用巡抚郭嵩焘荐,徵入同文馆,充算学总教习、总理衙门章京,授户部郎中、三品卿衔。”撮合之大者,为文化事业做贡献啊!
(二)大撮合家的性格缺点
大撮合家郭嵩焘哪儿都好,就是有一个性格缺点,太急躁。心理学上把人的气质类型进行分为四种。其中,多血质的人虽爱交际,喜欢与人交往,但是有个太急躁的缺点。郭嵩焘也许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清稗类钞》点出了郭嵩焘的性子,说他在家的时候言论就比较偏激。“湘阴郭筠仙侍郎家居时,好危言激论。”《清史稿》也多次记录了郭嵩焘急躁的性子。咸丰九年初的时候,英国人打到天津来,到皇帝家门口了,陪皇帝读书的郭嵩焘被派往和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共同筹划天津的军备。两个人意见不合,郭嵩焘一气之下就辞职了。“咸丰九年,英人犯津沽,僧格林沁撤北塘备,嵩焘力争之,议不合,辞去。”一言不合就走人,这是典型的郭嵩焘式风格,这也得罪了僧格林沁。
得罪了位高权重的人,郭嵩焘的日子不会好过。咸丰九年年十月,郭嵩焘又奉命前往山东巡视贸易税收情况并开办厘金局。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棻(字云舫)作为协办人员随行。巡视海关税收,自然免不了查出一些贪官污吏。而开办厘金局,其实就是对商旅收过路费,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得罪的是商人。开办厘金局不久,烟台厘金局就发生了厘金局人员被殴打的事情。十二月底,僧格林沁以郭嵩焘未与协办人员李湘棻、山东巡抚文煜商量,便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弹劾郭嵩焘。《咸丰朝实录》载:“兹据僧格林沁奏:该员(指郭嵩焘)前赴烟台,派委绅士设局抽厘,未能会同李湘棻查办,又未及与文煜面商。”咸丰十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忍苦耐劳,尽成一梦”。回到北京后,郭嵩焘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被冷落了。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抱怨说,跟各种王公贵族周旋,动不动就有言语方面的矛盾,“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是啊,谁叫你这么猴急呢!
咸丰十年四月,心情郁闷的郭嵩焘辞职回老家了。在老家住了两年,到同治元年三月终于坐不住了,主动给李鸿章写信想到上海来工作。李鸿章与郭嵩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喜欢跟洋人打交道,又都是曾国藩这条线的人,所以相互欣赏。李鸿章本来想让郭嵩焘来上海收关税,但是了解老朋友性格的曾国藩写信阻止说,郭嵩焘是个写书的好手,却不能实干的人才,让他来收关税,万万不可,“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若任以沪关,绝不相宜”。于是郭嵩焘就做了苏松粮道,帮助李鸿章在江苏和上海筹粮。同治元年,郭嵩焘去江苏之前,路过曾国藩大营,曾国藩赠送他一副对联:“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可能这个心灵鸡汤起了一点作用,这一年郭嵩焘表现不错,官运亨通。第二年,郭嵩焘升任两淮盐运使,六月,被两广总督毛鸿宾推荐,升任广东巡抚。
筹钱一直郭嵩焘的老本行,送咸丰三年跟着曾国藩办团练就开始了。这不,到了广东,做了巡抚,又手痒了,力行劝捐,开办厘金局。可能最近官运太顺,没有曾国藩的提醒,郭嵩焘又着急了,手段太凌厉,一时间粤商怨声载道。有人匿名作了一副对联咒骂郭嵩焘和毛鸿宾:“人肉吃完,唯有虎豹犬羊之廓;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沚之毛。”“廓”、“毛”骂得就是郭嵩焘和毛鸿宾。毛总督也是官场老手,把责任推给郭巡抚。郭嵩焘一气之下,在人前放出大喇叭:“曾涤生保人甚多,唯错保一毛季云。”要骂毛鸿宾,顺带捎上自己的老朋友曾国藩,哪有这么骂人呢?曾国藩既然是好兄弟,也没有生气,只是幽默地进行了口头回敬:“毛季云保人亦不少,唯错保一郭筠仙。”
(三)大外交家
郭嵩焘连曾国藩都敢得罪,想想还有谁不敢得罪,更别提左宗棠了。更何况郭嵩焘还救过左宗棠。可能就是心里这样想着,某个场合某句话冲撞了睚眦必报的左宗棠。左宗棠就没有那么宽宏大量了,咸丰三年年底,左宗棠以广东剿匪不力的借口弹劾自己的恩人郭嵩焘,并将其赶下了岗。
从广东巡抚下岗之后,在家闲居,咸丰五年又被召到北京,六年又短暂地做了几个月的老本行两淮盐运使,之后就没有做过官了,直到光绪年间。光绪元年,他终于不用跟筹钱的老本行打交道了,发挥出了身上另一个优点,即懂洋务,成了外交官。般来说,善于撮合的人一般都拥有开阔的思路和发散思维,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交际广泛,所以他也有一定的外交才能。清廷显然也看到了郭嵩焘这一才能。
这一年,他担任英国、法国大使,成为了中国首位驻外大使。“擢兵部侍郎、出使英国大臣,兼使法。”史书对郭嵩焘的外交才能给予了高度肯定,“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过去也有使节出使外国,像张骞出西域、郑和下西洋那些都不算驻外大使,他们只是去一趟就回来,不叫住驻国大使,郭嵩焘正儿八经的第一个在外国常驻的。

作为中国首位驻外大使,郭嵩焘在外交上也是颇有建树。早在咸丰年间,俄国就占据了伊犁。光绪四年,清廷派了崇厚去跟俄国人谈判,次年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没有收复全部领土,崇厚也因此被问罪。多数大臣们主张用武力赶跑俄国人,但是郭嵩焘不同意。他上疏提出了他的看法:派遣使者去跟俄国交涉,“遣使议还伊犁”。清廷觉得可行,便派了曾纪泽出使俄国,最后真的全部收回了国土,成为晚清外交史的唯一胜利。“已而召曾纪泽使俄,卒改约。”在大臣们都主战的情况下,郭嵩焘却如一股清风,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
(四)结语
光绪五年郭嵩焘就辞职回家了,在研究学问和讲学上,安度晚年,于光绪十七年去世。由于曾国藩曾经评价过郭嵩焘不是“繁剧之才”,曾纪泽可能也受了影响,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他用“花拳练步”四字来评价父亲的好友郭嵩焘。其实,郭嵩焘可不是花拳练步,他不知道撮合了多少好人好事,是名副其实的晚清大撮合家,至少在帮湘军募集资金这件事上出了很大力。
郭嵩焘的缺点可能就是太急躁,而这种急躁又杂糅着一股文人的清高,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记载,郭嵩焘说司马德操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却认为不被风气所染才是俊杰。“司马德操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吾则以不为风气所染为俊杰。”
也许郭嵩焘最应该去做的就是投行的承揽业务,或者干脆去银行零售业务。相信以他的撮合力,业绩一定没问题。不过后台的细致的落实方面,就不如他的朋友曾国藩有工匠精神了。虽然不适合做PPT,但郭嵩焘真的适合站在历史的舞台上侃侃而谈。